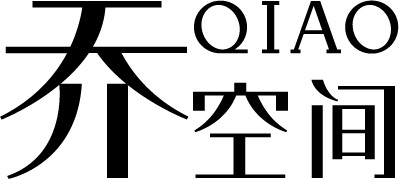对谈|讲座-“李燎:近乡情怯”答观众问
“李燎:近乡情怯”答观众问
《不知道20200205》
一
观众:刚刚仔细看了《不知道20200205》中的每个视频,这件作品特别打动我,我觉得它非常贴切地描绘了我在疫情期间的心情。我想请问一下杆子上的红色塑料袋可以被理解成红旗么,其中是否有包含一些政治性的表达?
李燎:政治性的表达并不是主要的。它可能更像是一个装饰,但内里不是政治性表达。之所以选择这个颜色,一是因为我们那边有个超市是当时疫情期间唯一开放的大超市,里面的塑料袋有两个颜色,我可以选择一个白颜色,我也可以选择红颜色的。如果说跟政治性有没有一点关系的话,它仅仅在于后面选择这个颜色的时候,觉得可能红色会带来多一个说法,但它绝对不是一个政治性是主旨的东西,绝对不是。它里面更加主旨性的东西,我觉得是人的动物性。其实我们一直活在一种安逸的情况下,但是当你碰到灾难的时候,人的动物性就会很快地展现出来,比如说大洪水或大暴雨来袭,乌云压城的时候,有些人会慌,但有人会兴奋;我是那种会感到兴奋的。以前我们那儿经常会有洪水,我初中的时候刚好是98年特大洪水,大家都在准备一板子一板子地去拖木料,或者要去囤一些东西的时候,我跟我的几个朋友特别喜欢骑着车在路上狂奔。心里会有很兴奋的感觉,冲上去了,在雨中冲上去了。所以这种感觉也是一样。城市里已经很荒凉了,但你很想到上面去嬉戏,去游耍。
观众:我理解,我老家那边一直有台风,很多人去追台风。 李燎:对,这其实是人天生的一种动物性。有一个艺术家,好像是叙利亚的吧(注释:李燎说的应该是Francis Alÿs,是比利时的,不是叙利亚),他会跟着去追台风的风眼,冲进去拍摄,我挺喜欢那个艺术家的。 观众:我在疫情期间看到网上很多视频都是关于动物占领了街道,然后你刚刚说到这个动物性,就让我觉得你会不会也有一种想要去占领街道的感觉? 李燎:肯定有啊,特别是双黄线这种很有代表性的符号,你能在双黄线上面走路的时候,很多事情已经很反常了,因为人什么时候能去双黄线上面走路,在上面像这样去玩杂耍。 观众:我其实也很好奇,每个视频前面都做了一个铁皮,它们跟视频里面很多城市基建中使用的材料其实也很像。所以你当时想要有一个这样的东西,选择这样的长度或者大小是有什么想法吗? 李燎:大小、长度的话只是因为它正好适合,它就是适合这个大小。再放大,就可能是另外一个感觉。 观众:我个人觉得有一个这样的装置,其实还挺改变观众的观看方式的。 李燎:当然做作品的时候是没考虑这些的,但是当我想着如何去展示的时候,就会开始追寻记忆中的,或者感觉上有什么样更合适的方式。这个蓝色铁皮是在疫情期间封路的时候使用的,比如说封我们家巷口的时候都是用这个蓝色铁皮搭一个大木架子,然后搬来一些铁皮,到处能看得到,包括视频里面也会很频繁看到这个东西,所以就觉得没有什么别的选择,这个是唯一的选择。它其实也造成了一种区隔,但另外,它也同样像一个通道。 二 李燎:这个作品是在疫情期间,我被困在老家洪湖时做的。当时封城了之后,整个路面上车也没有了,人也特别少,出门买点东西的时候,你就拿着通行证,去超市,整个城市都空了,你就发现你可以在马路上面走,因为没车。然后你在马路上走着走着就会发现,哎?还有双黄线,可以踩着双黄线上面。这种情境是以前碰不到的,双黄线的代表性我觉得还挺强的,我就觉得要在双黄线上玩一玩,杂耍一下。 这个也隶属于我的“不知道”系列,这是“不知道2020”,所以大多数时候我都没有一个具体的要表达的东西,我不知道,我就想干这些事。我在这个情景里面,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是我希望自己能做的。 观众:是觉得好玩吗?有这个考虑吗? 李燎:如果就简单讲的话,好玩肯定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有时候它不止是好玩,这也可以是一个作品。 观众:实际上抖杆的时候还是好玩的,这有练过吗? 李燎:我是去年演朋友的一个电影的时候,他让我玩了一下。当时我一玩,发现我玩得很稳。只要想我不让它掉下来,它就永远都不掉下来。可以玩到最后人都停止了,杆也停止了,进入一种放空的状态;我就盯着杆,周围全都虚化了。 《柔情》 李燎:做这个作品是因为我之前看到一个人带着一幅蓝牙耳机,对着一棵树在沟通。因为他戴耳机的时候,他是在跟对方打电话,对方肯定是在埋怨他,然后他觉得自己压力很大。因为一个中年男性,他处于职业的瓶劲期,有点不上不下的,在公司压力肯定很大,然后就说自己每天早上很早就上班,晚上很晚才回来,“你为什么不理解我一下?”“我那些事情,根本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等等。仅仅是因为上班的原因没来得及去解释那些事情,对方肯定就继续升级地去埋怨。这件事情就让他的情绪变得很激烈。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对这件事情本身是不太清楚的。但我站在旁边感动了半天。于是我就写了一个基础的剧本,主要是拿捏情绪。剧本的语言都很简单,只是把我记住的场景稍微写个脚本,然后情绪怎么上升到哪里,再往下降到哪里。 观众:我有一个问题,你今天开幕的这个演出,后面都有吗?还是说演员今天的这个行为会变成视频的形式? 李燎: 后面没有了,后面我会让观众变成演员。我会在上面放一个耳机,蓝牙的头戴式耳机,放在架子上,然后大家戴上一听,里面全都是各种拒绝你的声音。 观众:跟演员听到的是一样的吗? 李燎:演员的耳机里是没有音频的。 观众:那拒绝你的声音是从哪里来的? 李燎:我到处搜集的,找朋友录啊什么的。 到后面再来看,跟今天看的又不一样了,然后你就面对那棵树,就会听到各种拒绝的声音,感觉那棵树在拒绝你,你心里面就会“铛,铛,铛”地沉下去。 《不知道20191226》 2019年的时候,很多新闻报出来说猪肉很贵,然后这个手机就是一个最新款的苹果手机,当时最贵的iPhone XI pro。所以这两个东西在我看来有某种对等的关系——一个很贵的猪肉和一部很潮的手机,然后再配合穿着成流浪汉一样的角色在街上不停地去摩擦。旁边所有的拍摄都是伪装成路人的视角在拍摄,实际上是给予一种路上的观众的观感。就是说大概是因为看到一个很怪的一个人,很怪的一件事情,观众不知道是在拍摄,就故意让镜头隐掉。 《一记武汉》 观众:像你之前在国内做的那个扇耳光,还有《一记武汉》那样的作品,有没有一种对现有的规则的反抗? 李燎:有,所谓的这种荒诞的感觉,实际上就是把语境给突破一下,或者怎么样一下。但更多的,像我刚才跟观众聊的时候说的,作品里面一直都有两个卖的东西,一个是很清楚自己是在干嘛,一个是我也不是很清楚在干嘛。你像那个打的就有点不清楚是在干嘛,但又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想去做,但往往最后会很喜欢这种不知道要去干嘛做出来的东西。因为知道了之后它像是一个制作,就像之前我做了把自己锁在一个白领的楼下的作品的时候,其实我很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白领在上面上班,我被锁在楼下;我们是一个对等的关系,其实他们也是跟某些东西锁住的,这个逻辑关系能很清晰地解释出来。当然也有很多人喜欢,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这就是制作一件作品,区别还是有一些的。这个《一记》就是倾向于一种现实,或者平凡社会、平凡事件的一种荒诞。然后那种荒诞是……这个东西必然是一个日常的,不是说我做出一个戏剧的荒诞感,而是一个很日常的荒诞感;但这个日常的荒诞被拿到一个不同的语境来把它放出来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一个区隔,它的荒诞感就立出来了。 所以《一记》就很有这个意思,它的逻辑关系没那么大,像是说我到底要根据什么做件什么事情,没有这个的。反而是因为当时的情绪、情感关系,很多时候心情在那么一个调上,然后把这么一个日常里面很有情绪化的动作——扇耳光——拿到一个公共空间里面去,变成如同表演一样的状态,所以它本身就成了一种我所说的平凡事件中的荒诞。 观众:那你会觉得这跟地域有影响么? 李燎:会,你在不同的地域里,你感受到的这种环境上的气场还是不一样的。我明显在武汉是会很想去创作的,所以我后来一直说我尽量避免去武汉。因为很想创作这个事情,好像有点问题,你知道吧?你对一个欲望性的人,比如很喜欢一个女人,就要跟她稍微隔开些,你不能天天说我们怎么样怎么样,那就没意思了,就这种感觉。 观众:这个展览也叫“近乡情怯”,它也是跟地域性有关的? 李燎:对。
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