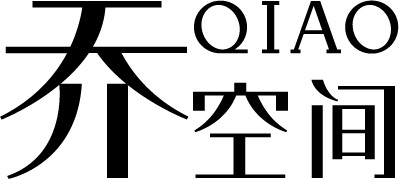采访|李燎:近乡情怯
乔:乔丹
李:李燎
乔:可以先聊一下《不知道》这个系列,比如说《不知道20191226》《不知道20200205》这两件作品之间有什么联系,以及是怎么开始了这一系列的创作。
李:这个系列开始是基于我结束了一个长期项目的制作,刚结束之后就想到要做这么一件事情。之前做了两次长期项目,都是接近两年的时间段的这么一个事情,一直在很琢磨、很系统地去做,很关注这整个作品的逻辑,还有它的表达以及它自己跟自身的关系,想得特别清楚,要不然也不会花这么长时间去做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就是那个时候觉得作品的逻辑完成度还原得过于高了,做完了以后就不想去接着那样去做了,当时想做一些另外的东西。包括我一直以来的创作里面都会隐隐有一些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做但是又挺喜欢的东西,到后来也会有,但后来慢慢地就是说做作品会更加地考虑它的可解释性,或者说可被阐述的方式,考虑的这些东西想想没必要的,我觉得你喜欢就是喜欢,喜欢就去做呗。后来也有很多方案就想去做,最后就搁置了,觉得没想清楚,但现在我觉得“没想清楚”它本身可能是一个指引我的东西吧,自己是应该要把它做出来,它不是你非要把它想清楚才去做的。所以,我让这件事情变得合理的方式呢,就是我启动了一个计划叫做《不知道》系列,我就多做一些这种我也没弄明白,我也不知道要干嘛,但我就想做这些事情,它可能大部分就是一些轻体量一些的作品,靠我自己就可以完成,然后随时想到随时就可以去做,所以一般是偏小的、偏轻的、时长可能也会偏短的这样的作品。它有可能不是所谓的行为或者是视频,有可能就是个什么东西,所以这样的东西可能会成为我接下来创作的常态,我希望《不知道》这个系列它是可以占据我的大部分的闲暇时间,因为我总感觉我有点过于闲了(笑),感觉挺懒的。这样就是好像你在执行方案的时候你就在拼命去弄,好像在不执行方案的时候感觉人不知道干嘛。然后每天看着老婆去上班,自己呆在家里面,这两年做长期项目就给自己找了一个由头,健健身,学英语(笑),反正模拟他们在上班一样,加上这个项目也到一个阶段了,我还是想能让自己有一个想象中的工作状态,所以这个《不知道》系列可能会让自己平常就能像工作一样。
乔:那《不知道20191226》我们可以看到展览的方式拿这个铁皮一个一个框,观众需要从这个框里面看到这个屏幕上的内容,这个是怎么想到这样的呈现方式? 李:《不知道》从创作方案规划的时候是“不知道”,后面的就比如说展示,如何去贴近作品本身去展示的话就还很明确的,是知道自己是要干嘛。所以选择这个铁皮,包括让人再去看。我是因为这个作品是在疫情期间,疫情高发的城市就我们老家在那里做的,封城的时候路面上很多那种围栏把我们的街道都直接拦住,因为我们那不是单元楼,关个门就可以了,是需要打那种木架子,附上这个铁皮然后把我们拦起来。大量地能看到这种铁皮,因为我会偷偷跑出去,看到这个铁皮就觉得挺有趣的,包括也做了这件作品。其实我在用这个铁皮的时候,还没有想到它跟这个作品的联系,所以方案逐渐成型的时候发现要去做这么一件铁筒的时候,发现视频里好多这个蓝色的铁皮,就觉得对了你就这样想,这个可能就是“不知道”的魅力了。它是一个就活在那个气氛里的时候,你以为你需要去想,其实你在选这个东西的时候,它在那个环境下就是——按人来说就是潜意识,按机器来说就是缓存。缓存已经把这个东西缓存进去了,你其实不用去特意创造一个东西。所以呢铁皮就特别合适。然后做成一个筒,是故意地造成一个隔断,我觉得这个隔断看似是一个通道也好,或者是一个故意让你不走进也好的,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有趣的事情。包括在观众们看的这边是一个刀口,那么它是时不时提醒你危险性的存在,拒绝你的一个存在,想要你不要那么靠近、但是又能通过一个小的通道去看到那个东西。 乔:那么另外一个《不知道20200205》那件,看到你在视频拿着一个新的苹果手机和一块猪肉,怎么想到这两点出发做的联系? 李:那个时候听到新闻说猪肉挺贵的,去年19年猪肉特别贵,都要吃不起猪肉了;另外一个就是新出了苹果iphone11 pro,是最贵的一个手机。现在觉得这个手机它已经脱离了一个本身的使用工具的范畴,它变成了至少对大部分人来说是一个时尚的单品。它好像比衣服更时尚,衣服可以换来换去,好像大家都有那么一个东西,然后它价格也不菲,一个小的手机一万这样,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就有某种联系,或者某种相似性、对称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在大街上把自己弄成一个乞丐的样子,然后把这两个我认为最贵的东西去摩擦。其实这个方案我之前也有过类似的想法,想在这种电子设备上抹油的这种感觉,我觉得用一块肥猪肉这样抹会更好。 乔:所以就当时拍的时候在深圳的地铁上你有预想路人会有什么样的反映,或者是还没有设预想? 李:其实我的预想是别人都会很好奇这件事情,因为一个乞丐会拿着这两样东西,一个那么贵的手机,一个一块鲜猪肉,可能会是一个很怪异的场景。深圳人民有点太超出我的预想,大家毫不关心这个事情,基本看到的也把眼神偷偷挪开,保持一种我默默的体面,我觉得深圳这个城市里面有一种要保持自己就是不是大惊小怪的人,自己不会对一个弱者也好,怎么样也好保持一个过多的关心,因为会打扰到别人或是怎么样。大概就是这样的。 乔:然后还有一件作品,就是现场这个表演的作品《柔情》,这个是因为突然看到这个景象想出来的么? 李:这件作品当时另外两件作品已经成形了,已经提交方案了,这中间我在小区突然碰到了这么一件事情,当时我是被感动了,真真正正被感动了。被感动这件事情就是这样,我去小区楼下取个快件还是什么,看到一个人对着树在说话,情绪会越来越激烈,说的内容大概就是对方不理解他,他上班很累,压力很大,他也到了一种不上不下的一个年纪,公司的地位也是这么不上不下,然后居然你还不体谅我,他要撑不下去了,很歇斯底里地。但是从头到尾他是戴着一个蓝牙耳机,对着一棵树,你就会看到是一个人对着一棵树在发狂,哭泣,然后到最后就发呆这种感觉。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场景太棒了,我就不用改它了,我就直接想办法挪到展厅里面就挺好的。 乔:我稍微跳过去一个问题。《不知道20200205》那一件在开始这个《不知道》系列后怎么就想到追红色塑料袋这个想法? 李:其实是整个城市突然空了,在路上走路的时候突然发现路面也没有车,人在马路上走也可以,甚至压着双黄线走路也可以,以前听到好像压着双黄线是最流氓的,我也可以走双黄线呀。然后就是加一点好玩的东西嘛,刚好就是去年我去演别人的一部电影的时候,导演让我玩了这样一个顶杆子,突然发现我有这样的基因你知道吗,我比谁都顶得好(笑),我甚至可以站着不动,杆子不动,手也不动,就那样定在那里。而且我顶杆子的时候发现我会入定,就是你会看着一个杆子中间的局部,周围全部变成盲区,你就会有入定那种感觉。这种感觉太好了。所以我在想,双黄线我也能上去,那我在双黄线上玩这个。顶个红色的塑料袋就是一种小趣味。 乔:最后就是关于这个展览题目吧。比如说《近乡情怯》是不是也代表“不知道”或者有包含不确定性这么一个因素的想法? 李:它实际上就是故乡嘛,它是一种长期别离之后回去短暂休息的一个状态,呆个两三天没事,要真把你放在那里呆个一个月两个月,那真的会慌的。这次因为外部的原因你就必须要呆在那里,虽然也确实挺开心,但是也确实挺慌的。很慌是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事情到底会变成什么样,我觉得这个事情肯定是新世纪以来成为很大的一个分水岭的事情,人们终于面对了一个完全真真切切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事情。 乔:补充还有一点就是《不知道20191226》和《不知道20200205》这两件作品心路历程以及关系。 李:这两件作品本来是没有联系,它只是随着这个系列,创作的动机和心态都是“想做就去做”,都是这样做的,但它达成一种巧合,将它们摆在一起,会觉得这个巧合就挺有趣的。2019年末,我在深圳装成一个乞丐在大街上这样去走;然后2020年,在老家的街头那样去走。其中一个是人非常多的状态,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孤苦伶仃的乞丐;另外一个城市里面都没有人,在城市道路很荒诞地嬉戏,这两个像天平的两侧一样,形成很对等的一种。
相关内容